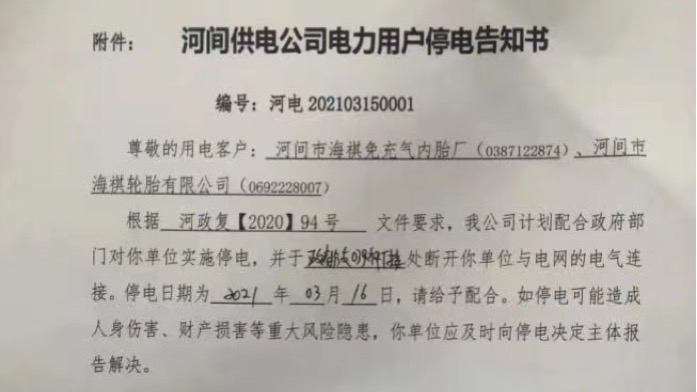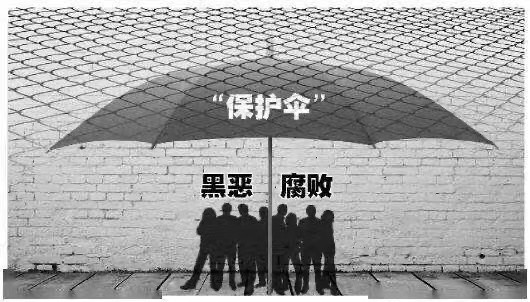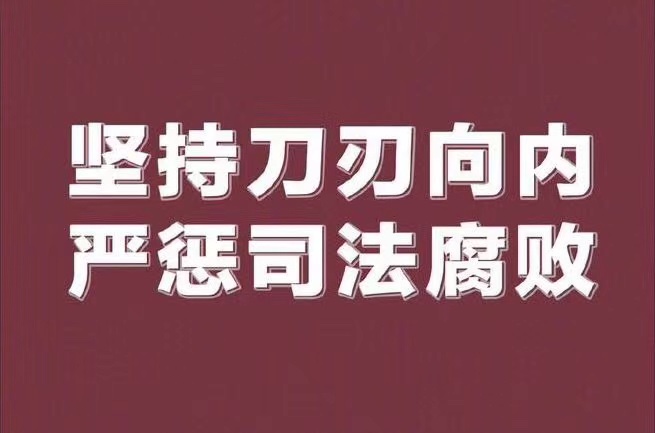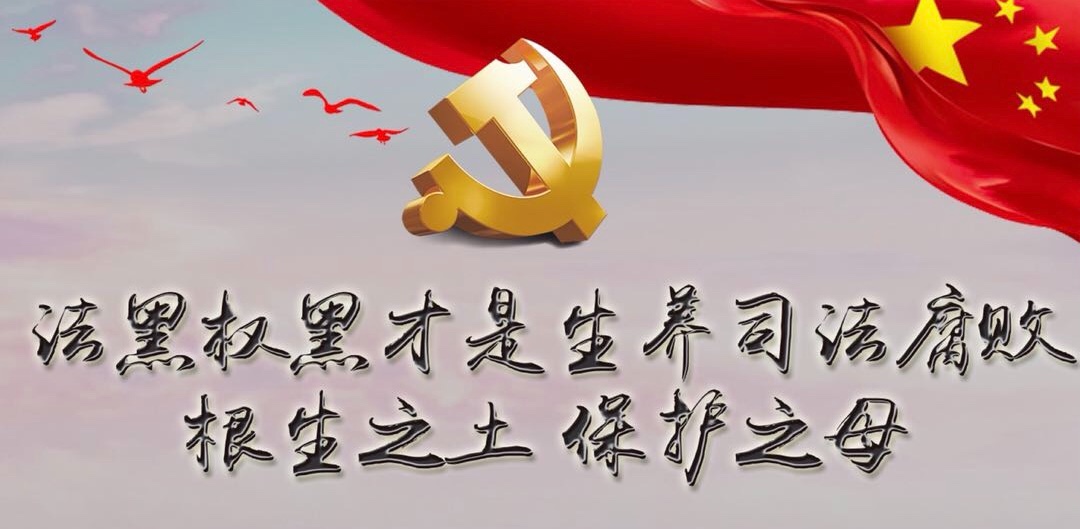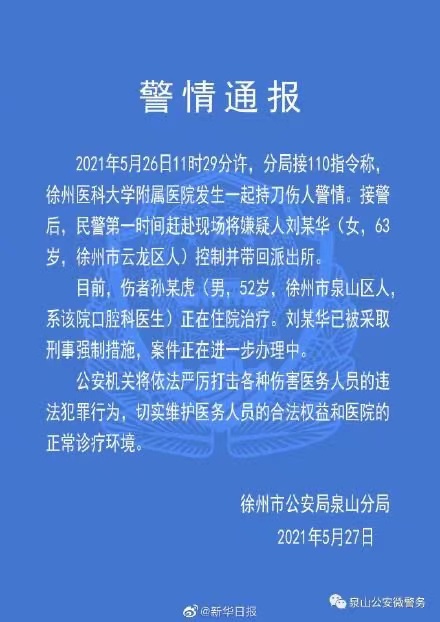疑罪从无的边界:曹亚胜案背后的刑事正义困境

刑事司法领域的疑罪从无原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,但在实践中却屡遭挑战。广东廉江市“林为杰涉黑案”中,同案犯曹亚胜的“被卷入”案件,充分暴露了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缺失与司法公正的摇摆。一个被“黑老大”亲自喊冤的“马仔”,是否真如判决书所述参与了犯罪?
案件回顾:定罪背后的疑问
曹亚胜,年过半百,未婚无育,长期在外地务工。2021年,他因被指控参与一起发生在2011年的绑架、敲诈案件,被广东廉江市法院认定为“林为杰涉黑组织一般参加者”,并获刑十七年六个月。然而,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,曹亚胜不仅否认所有指控,连主犯林为杰等十余名同案犯和多位被害人均称“不认识”曹亚胜,案件证据也疑点重重。

据一审判决书,曹亚胜的犯罪行为仅限于被指控在林为杰的指使下“对未成年人殴打并强行灌水”。然而,这一核心指控的证据,包括供述、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,在庭审中被多次质疑甚至翻供。
疑点一:证人证言的矛盾
案件中,钟亚文和陈烈敏是唯一在侦查阶段指证曹亚胜的人。然而,庭审时两人证言出现重大反复:陈烈敏当庭翻供,称不认识曹亚胜;钟亚文则在供述中自相矛盾,关于曹亚胜的衣着、身份等细节均无法自圆其说。
更令人诧异的是,关键证据的形成过程也存在问题。陈烈敏首次指证曹亚胜的讯问笔录,被律师发现存在“侦查人员代笔”嫌疑。这种情况下,相关证言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。
疑点二:被害人的改口与压力
案件中,被害人曹厚杰、邓欢分别指认曹亚胜,但两人先后表示,他们的指证是“警方安排的结果”。曹厚杰更是在案发十多年后,因拒绝指控其堂叔曹亚胜而遭警方以“包庇罪”威胁。最终,他在警方压力下改口,但后续多次书面声明,称曹亚胜未参与犯罪。
另一名被害人邓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因事发时年仅14岁,案发过程记忆模糊,其辨认曹亚胜的行为“是警方主导下完成的”。这些供述让人不得不质疑,控方是否在刑事侦查中存在“强迫证人供述”的问题。
疑点三:不在场证明的忽视
辩方提出,案发期间曹亚胜人在广西务工,证人倪洁芳、李婵娟等人出具证言,证明曹亚胜正在装修房屋。然而,二审法院以“证人无法证明曹亚胜一直不在现场”为由,未采信这些证言。这种“举证责任倒置”的做法,令辩护律师指出:“刑事诉讼中,排除合理怀疑是控方的责任,而非被告人证明清白的义务。”
疑点四:案发经过的逻辑不合
曹亚胜被指控“灌水”等行为,但无论从案发背景还是事后发展来看,他的身份均显得突兀。作为一个长期在外地务工的普通人,他如何在毫无前科的情况下突然“出现在”涉黑组织中,完成犯罪后又“销声匿迹”?这种“逻辑断层”让人难以置信。
法律程序的僵局
2023年以来,辩护律师团队不断向广东省高院申诉,试图启动再审程序。但案件的进展缓慢。广东省高院在2024年受理申诉后,仅以“延长审限”为由拖延至2025年。律师指出,案件背后可能涉及侦查部门的“错案不纠”,甚至是“利益勾连”。
反思与启示
曹亚胜案并非个例,其背后折射出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规则的失灵与司法程序的僵化。案件疑点包括:
1、证据采信的随意性:相关供述的形成过程、内容逻辑均存疑,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。
2、举证责任的转嫁:法院将证明无罪的责任推给辩方,违背无罪推定原则。
3、申诉机制的疲软:再审程序迟迟未启动,让案件陷入司法拖延的泥沼。
总结
正义的延迟等同于正义的缺席。曹亚胜案的疑点早已足够支撑再审的必要性,但司法机关却迟迟未有实质性动作。案件的最终结果不仅关系到曹亚胜个人的命运,更事关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。希望这起案件能唤醒社会对刑事正义的更多关注,推动疑罪从无原则的真正落实。
作者|朱辉
编辑|程军
声明|本网站发布此文旨在传递更多信息,若您发现内容有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立即致信jinrizhiyi@gmail.com,我们将迅速核实并进行更正或删除。感谢您的监督与支持!